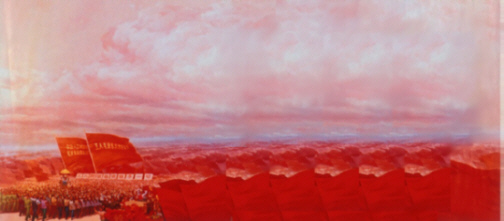
|
走出紅海 汪成用 (一) 本來是早該出名的。可運氣不好﹐“成名作”所歌頌的對象曇花一現。他自己短命不說﹐還耽誤了我出名。 (二) 一九七六﹐多事的一年。 那時的國人﹐個個像神經崩緊了的兔子。人們機警地從報上的字裡行間捕捉弦外之音﹐再驚弓之鳥般地衍生出顛覆性的小道新聞。儘管一再“辟謠”﹐“謠言”卻多數成真﹐兔子們便更加機警。可當“中央抓人了”[1]的“謠言”傳來時﹐因其顛覆性大大超出了國人的平均承受力﹐人們還是嚇得不敢相信。記得是一個姓張的老師傳話給我的。老師的父親是省級幹部﹐很有些通天的消息。他說此話時的神情使我相信一定是出了大事。他的眉毛擰成一團﹐嘴唇發抖﹐說不上是激動還是恐懼。 直到“特大喜訊”印成了鉛字﹐御林詩人以走了調的興奮“大快人心”﹐人們才如夢初醒地蜂擁上了街。再後來﹐是眾人圍在電視機前等待我們的“新救星”登基的聖典。按照傳統﹐領袖現身時必鼓樂齊鳴。新救星當然要有新音樂﹐可不知是粗製濫造﹐還是別具匠心﹐新曲的前奏竟與唱“老救星”的老曲前奏如出一轍﹐給人一種老救星起死回生的肅穆與莊嚴。就在滾瓜爛熟的曲調馬上要沿著慣性脫口而出的一刻﹐旋律突然由本應順理成章的《東方紅》[2]﹐峰迴路轉地巧變成了《交城山》[3]。與此同時﹐踩著拍子踱步而出的﹐是英明的領袖華國鋒﹗
第一次如此深切地感受了音樂的超功能。民歌﹐太玄妙了﹗僅幾音之差﹐升太陽的地方便由陝北遷去了山西。清楚記得﹐一個頗有名氣的作曲家激動得喊了起來﹕聽﹗這就是新時代的《東方紅》﹗ 一個“東方紅”時代。如果沒有熱情的歌頌﹐音樂便沒了語言。而一旦有了歌頌的熱情﹐喋喋不休的就不僅是音樂﹐你的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像上足了發條充足了電﹐持續地興奮過度。 就在領袖登基的那一過度興奮的時刻﹐我立了個大志﹕寫一首史詩性的交響曲。 (三) 翻開張老師規定的必讀作品《森林之歌》﹐屝頁上的文字讓人肅然起敬。這是偉大的蘇聯作曲家肖斯塔克維奇[4]在接受了“黨與群眾的批評”後的脫胎換骨﹐歌頌的是史達林領導下的蘇維埃的植樹造林。當樂曲在“光榮屬於列寧的黨﹐光榮屬於英明的史達林”的合唱中輝煌結束﹐激動中生出個不該問的問題﹕他為什麼受批評﹖老師吞吞吐吐﹐似乎有種難言的神秘。隱約聽說﹐他好像是犯了“形式主義”﹐二十九歲就寫了個“反動歌劇”……。話題馬上有聲有色地轉向了“但是”﹐──但是﹐肖斯塔克維奇終於認識了錯誤﹐成為“黨的忠實兒子”﹐“共產主義的偉大戰士”云云。 假如當初就知道﹐“形式主義”不過是整肅文化異己的“何患無辭”﹐多少藝術家因此去了古拉格﹐甚而消失在西伯利亞荒原﹐我從輝煌中感受到的﹐就無論如何是一種扭曲。認識只能與時代同步。回到沒有“假如”的當初﹐對森林的全部認識﹐是綠色的生機盎然與建設者燦爛的笑容。 陶醉於《森林之歌》那史詩般的氣派﹐我構畫著交響曲的草圖。 (四) 然而﹐一九七六遮不住歷史。從陶醉中醒來﹐我有幸知道了“但是”之前的故事。
揮霍不完的才華加如日中天的名氣﹐二十九歲的肖斯塔克維奇正值人生的峰顛。千不該萬不該不該舞文弄墨﹐從而把音樂的優勢──解釋的隨意性──喪失貽盡。讀了列斯科夫的小說《麥克白夫人》﹐他決意寫一部歌劇。可聰明過度的他不甘於僅僅作曲﹐而是從腳本開始寫起。給他惹出大禍的﹐是女主人翁卡捷琳娜﹐一個丈夫性無能的下層婦女。她在孤寂中偷情﹐被常對她性騷擾的公公抓住了把柄。她害死了公公﹐又與情人合伙殺了丈夫﹐為此兩人同被發配西伯利亞。可情人背叛﹐又尋新歡。卡捷琳娜把情敵推入冰河﹐而後自盡。肖斯塔克維奇在劇中嘲笑了除卡捷琳娜以外的任何人﹐卻對一個“殺人的淫婦”充滿同情。 《麥克白夫人》的上演引起了不折不扣的轟動。短短兩年﹐演出超過一百場次﹐世界樂壇也為之震驚。 肖斯塔克維奇的摯友﹐偉大的大提琴家、指揮家羅斯托科維奇曾說﹐他被卡捷琳娜式的“扭曲的人性”所深深地震撼。問題就出在這裡。托爾斯泰的現實主義揭示的是人性﹐高爾基的“社會主義現實主義”則宣揚革命。顯然﹐肖斯塔克維奇筆下的卡捷琳娜已完全“托爾斯泰化”﹐由是﹐他墮入了一個賴不掉的結論﹕背棄了蘇維埃給現實主義下的定語──社會主義。 一場厄運已在劫難逃﹐年輕的肖斯塔克維奇在一九三六年的一個冬日裡幾乎徹底崩潰。那天早上﹐當不溫暖的太陽像往常那樣昇起﹐《真理報》以顯著的篇幅發表了重要社論﹐對歌劇《麥克白夫人》進行了猛烈的批判。更糟的是﹐他以作曲家特有的敏銳透過字裡行間聽到了弦外之音﹐一股陰冷的史達林味。幾天前領袖曾親臨劇場觀看了《夫人》﹐並在結束前拂袖而去。再清楚不過了。讀著報他雙腿一軟冷汗如注﹐沒什麼能形容那種絕望的恐懼。那些日子﹐他把生活用品收拾在一個小皮箱裡﹐隨時等待著秘密警察的光臨。從此﹐他就再也無法擺脫史達林的陰影。 三十年後﹐當記者問起他的近作﹐剛完成了兩部弦樂四重奏的他臉部肌肉抽搐了幾下﹐顧左右而言他﹕“我……最近在為電影《卡爾•馬克思》寫配樂……”話頭就此打住﹐他奇怪地歪著嘴﹐手指像敲鼓樣地在桌上打著拍子。警覺已溶入血液。他似乎在手指敲打的節拍中習慣地等待。 等什麼呢﹖以一言概括他二十九歲之後的生命﹐即﹐等待毀滅。 史達林終於饒了他一命。可等待一個打不出來的噴嚏要比噴嚏本身痛苦百倍。據說﹐噴嚏之所以沒打出來大概有兩個原因﹐其一﹐他的名氣太大﹐以至羅斯福也為他說情。其二﹐史達林高瞻遠矚﹐認准將來還用得著他。也許二者皆有﹐但歷史證明了後者更為可信。如果二十九歲的肖斯塔克維奇被送去了古拉格﹐也就不會再有輝煌的《森林》。 在等待的節拍中﹐他用手指敲打出綠色的死裡逃生和建設者心驚膽顫的笑容。 (五) 你一定記不起母親的第一次微笑。就像我記不起是什麼時候第一次聽的《交城山》。依稀記得﹐它是從五十年代的一個歌劇中風靡起來﹐十幾歲的姐姐便成天价哼著“交城的山來交城的水……”。如花似玉的郭蘭英[5]是交城山與我相連的媒介。她演唱時的表情眼神﹐賦予山水以超越詞曲的靈魂。久而久之﹐郭蘭英便成了歌的一部份。本色的歌加本色的人﹐那魅力就沒法擋得住。那會兒我大概還穿著開襠褲﹐竟也會染上些“郭蘭英崇拜”。 後來才知道﹐《交城山》是明清時期的老調。交城﹐山西呂梁山東側的小縣。窮山惡水有其原始的誘惑﹐我迷上了它的拙樸﹐那一抖落就掉渣的土味﹕ “交城的山來交城的水﹐不澆那個交城澆了文水。灰毛驢驢上山灰毛驢驢下﹐一輩子也沒坐過好車馬。交城的大山裡沒有好茶飯﹐只有攸面烤姥姥還有那山藥蛋。”幾句家常話﹐竟能唱得鼻子發酸。似秦腔般的高亢﹐如晉劇樣的婉轉。交城雖窮﹐卻窮得楚楚動人。貧瘠的水土又養人﹐又養曲。 穿著開襠褲傻聽“郭阿姨”唱歌的我當然想不到﹐《交城山》竟在火紅的一九七六發得這般紅火。交城﹐便姑娘出嫁似地坐著轎子進了京城﹐只因“英明領袖”系山西交城人。文革中吃足了苦的郭蘭英重煥青春﹐在荒蕪了十年的舞台上再唱《交城山》。記得電視上的她雖仍有幾分風韻﹐但與小時候崇拜的郭蘭英已判若兩人。也許是因受迫害﹐在本不該五音不全的年紀﹐“郭阿姨”已有些上氣不接下氣。可她的演唱卻迎來了狂風般的喝彩﹐原本一張嘴就冒山藥蛋味的詞曲也亮出了新風景﹕ “交城的山來交城的水﹐交城的山水實在美。交城的大山裡出了游擊隊﹐游擊隊裡有咱們華政委。” “委”字還沒出口﹐一陣歡呼已淹沒了歌聲。雖然沒趕上從《芝麻油》裡提煉《東方紅》[6]的年頭﹐可有幸趕上了新《交城山》的歲月。能稱得上“英明領袖”的多少年出一個﹖千載難逢﹗隨著高八度的“華政委”拖出漂亮的甩腔﹐一個靈感讓我激動得坐立不安﹕我要用《交城山》作為交響曲的主題。 在郭蘭英沒完沒了的謝幕與扑天蓋地的鮮花掌聲中﹐我鄭重地寫下了交響曲的標題﹕呂梁山回想曲。 (六) 對《麥克白夫人》的圍剿以肖斯塔克維奇急中生智的“認錯”而暫停。 那兩年﹐身邊的藝術家一個個蒸發﹐苟活的也噤若寒蟬。驚恐之中﹐他被逼出了另一番聰明﹕用第五交響曲回答“黨與群眾的批評”。世上大概沒幾個人有如此認錯的本錢。以交響曲的身段認錯﹐無疑說明了他的大徹大悟。你可以從音樂中聽出喜怒哀樂﹐但你絕聽不出喜怒哀樂的理由。在無法解釋或任意解釋的情感背後﹐是肖斯塔克維奇還原自我的廣闊空間。今天﹐第五交響曲已被列為經典﹐可有誰能從中聽出他的懺悔﹖在他死後出版的回憶錄《見證》中﹐他辛辣地為第五作了腳註﹕“那是威脅下的喜悅。像是有人拿棍子敲著你的頭說﹕你真快活﹗你真快活﹗於是﹐你顫抖著跳了起來﹐一邊大步前進一邊念念有詞﹕我真快活﹗我真快活﹗”。史達林羞辱肖斯塔克維奇﹐肖斯塔克維奇便愚弄史達林。 合上苦澀的《見證》﹐雲霧裡的肖斯塔克維奇便走出迷團。他把固執的“夫人情結”與永恆的“史達林陰影”化成三種痛苦的語言﹕揭示內心世界的晦澀語言是自我的﹔作為“社會主義作曲家”的頌揚語言是表態的﹔電影配樂中的通俗語言是糊口的。他不得不浪費三分之二的生命﹐以保住三分之一的真誠。
歷史在原地打轉。十二年後﹐史達林一聲咳嗽﹐文化界遂展開了對《夫人》的又一輪批判。此時的肖斯塔克維奇已久經摔打﹐練就了一身在險境中與狼共舞的絕技。他學會了節省感情的“深刻檢討”﹐用報上比音樂更美妙的語言口是心非地作保證。經歷著卡捷琳娜式的痛苦﹐孤獨﹐無奈。知己一個個死去﹐朋友背叛﹐精神迅速老化﹐幾乎天天頭痛﹐他想到了自殺…… 再寫個交響曲“認錯”恐怕已混不過去。為給自己貼個“社會主義”的標籤﹐森林在夫人的痛苦中分娩。──“我們是普通的蘇維埃人﹐共產主義是我們的光榮。假使史達林說要這樣做﹐我們就回答領袖﹕就這樣。”[7] 事後他一再說﹐寫《森林之歌》實出于被迫﹐他為此感到丟臉。
覆水難收。他的“丟臉”卻引來了半個世界的喝彩。《森林》於四九年上演﹐隨即在五一年被譯成中文﹐從此影響了中國幾十年的合唱創作。──“勝利的旗幟嘩啦啦地飄﹐千萬人的呼聲地動山搖。史達林﹐毛澤東﹐象太陽在天空照。”[8]…… 史達林的死使他喘了口氣。但僅一年之後﹐他因第十交響曲再次受到批評。大棒之後又被喂了根胡蘿蔔﹐《森林之歌》被官方定為了蘇聯音樂的“樣板”。套用一句中國的老話﹐這叫“以己之矛克己之盾”。 帶著幾分嚴肅的滑稽﹐疲憊不堪的肖斯塔克維奇苦笑著用左臉批判了右臉。 (七) 可沒人強迫我寫《呂梁山》。 懷著滿腔的興奮過度﹐我從肖斯塔克維奇口是心非的苦笑中汲取養分。鋼琴上敲打出營養不良的自我陶醉。無知者無畏﹐一代感情的富翁﹐信息的窮人。 又是張老師神秘地向我透了點風聲﹐襁褓中的《呂梁山》居然被一九七八年的“上海之春”音樂節選中。 我忐忑地去見了名指揮家陳燮陽。被我從午睡中叫醒﹐陳指揮顯得很不高興。他睡眼惺忪地在鋼琴上讀著譜子﹐半醒之中敏銳地挑著刺兒﹕“銅管和弦怎麼沒三音﹖”“大提琴幹嘛和長笛奏同度﹖”……。我結結巴巴﹐滿頭冒汗。指揮心一軟﹐打著哈欠拿起了筆﹕“好吧﹐我幫你改。”幾個哈欠後他漸入佳境﹐琴聲也隨之入耳。 如果指揮是時代的鋼琴家﹐《呂梁山》就是個合格的琴鍵。 (八) 你﹐生活在一齣活的歷史裡﹐一齣驚心動魄的歷史。可你卻麻木得沒有一點歷史感。因為你不知道﹐沒有能力知道週圍發生的事情。你像井底之蛙讚美著藍天﹐可說不定井邊正在流血。當這一節歷史已被寫進書裡的多年之後﹐你從井裡跳了出來。驚訝憤怒﹐目瞪口呆。如果有選擇﹐你唯一的願望是﹕重活一遍。 (九) 一九七八年的春天﹐當“上海之春”在掌聲中啟幕﹐指揮家羅斯托科維奇在法國宣佈了一個重要決定﹕重演被禁了四十年的《麥可白夫人》﹐以告慰三年前死去的肖斯塔克維奇的亡靈。 三月中的一天﹐羅斯托科維奇在他巴黎的寓所裡忽聽見隔壁房間傳來妻子的驚叫。從新聞中獲悉﹐他們夫婦倆已被蘇聯當局吊銷了蘇聯國籍。幾天後﹐當動身去倫敦指揮一個蘇聯歌劇時﹐他們已不再是蘇聯公民。天下著雨。潮濕的平靜中﹐他們相依為命。 《麥可白夫人》的排練在戲劇化的尾聲經歷了陣痛。當卡捷琳娜將情敵索耶卡推入河裡﹐索耶卡應發出一驚天動地的吼聲。這聲吼對羅斯托科維奇至關重要﹐他固執地尋找著久等的畫龍點睛。可儘管一再努力﹐扮演索耶卡的演員還是叫得像夜鶯。休息時﹐唱片製作人格魯波對心事重重的羅斯托科維奇說﹕“看來你得想點其他辦法。”羅斯托科維奇一言不發回到舞台﹐開始逐一打量每個合唱團員。他的目光停在一個長著薄薄的嘴唇與刀一樣的鼻子的臉上﹐相視的一瞬﹐他似乎找到了感應。“請原諒﹐小姐”他溫和地說﹐“如果我讓您像臨死的野獸那樣大叫一聲會毀了您的嗓子嗎﹖我要的是您離開這個世界前最後的聲音。”小姐猶豫了片刻﹕“讓我試試。”
排練開始。卡捷琳娜一把將索耶卡推入冰河。一陣柔弱的心跳似的撥弦聲中﹐指揮棒所指之處﹐突然傳來一聲撕心裂膽如野獸般垂死的吼叫。那聲吼簡直能讓山崩地裂﹐冰河解凍。 全場震驚﹗ 羅斯托科維奇呆站著。 片刻死寂之後﹐格魯波沖過來緊緊地擁抱著他﹐哭了。 他們聽見了什麼﹖世界聽見了什麼﹖是羅斯托科維奇對當局侮辱藝術家的遲來的憤怒﹐還是肖斯塔克維奇憋了一生的早熟的悲慟﹖是一個時代臨死前喪心病狂的掙扎﹐還是人性在春天陽光下艱難的甦醒﹖ 而就在這一聲讓世界哭泣的吼聲中﹐上海音樂廳的舞台上﹐陳燮陽瀟灑地一甩頭髮﹐《呂梁山回想曲》在激情中達到了高潮。“交城的山來交城的水﹐游擊隊裡有咱們華政委”…… 冬末﹐森林已然死去。 初春﹐夫人正在重生。 我坐在井底﹐觀賞著頭上的藍天感動。 (十) 《呂梁山回想曲》讓我風光了好一陣。有人居然一本正經地告訴我﹐以畢業作品出名的﹐自鴉片戰爭以來只有兩人﹕辛滬光的《嘎達梅林》﹐我的《呂梁山》。 對鴉片戰爭時期的音樂史我太不熟悉﹐可此話讓我七上八下地犯起了嘀咕。嘎達梅林畢竟是已刻上墓碑的蒙族英雄﹐而華國鋒卻正在鋼絲上走得一臉的驚險。果然﹐政壇風雲無常﹐不到兩年﹐“華政委”又悄悄改回了“山藥蛋”[9]。《呂梁山》就此壽終。 幾年後我見到了辛滬光。以《嘎達梅林》出名後﹐她婉拒了留校任教﹐義無反顧地去了內蒙。遇見她時﹐這個北京女杰已完全“嘎達梅林化”﹐舉手抬足張口閉口都透出蒙族歌舞的韻味。因“鴉片戰爭以來的兩人”之說已沒人再提﹐我終於沒敢稱她一聲“師姐”。 不管怎麼說﹐《森林之歌》為肖斯塔克維奇贏得了“史達林勛章”和可觀的獎金﹐《呂梁山》卻沒給我帶來半分文。倒是由此生出的一個惡作劇使我哭笑不得地小有收益。在文化宮拉琴的朋友小齊﹐為追求一個拉琴的女孩子想出個浪漫的詭計﹕求我為他寫首小提琴二重奏以參加全市彙演。捲入“醉翁”的陰謀﹐我從《呂梁山》中胡亂抽出兩個聲部編成一曲﹐小齊還為它起了個時髦的名字﹐“長征路上憶呂梁”。也許是帶著別有用心的激情﹐此曲竟獲第一名﹐獎金高達五十圓。不料好事多磨﹐有個明白人咬定此曲剽竊了《呂梁山》。小齊捶胸頓足地保證絕無此事﹐組織人只好找《呂梁山》的作者拍板。忽聞有人到訪﹐說明了來由我忍俊不禁。裝模做樣地看了遍自己寫的譜子﹐遂揮筆寫了個證明﹕此曲雖與拙作使用了同一民歌﹐但並非剽竊。特此證。 當晚小齊興沖沖請我吃飯﹐當然還有那個蒙在鼓裡的女孩。我們開懷地說笑吃喝﹐盡情揮霍著五十塊錢﹐《呂梁山》倒也一時有了幾分可愛。 酒足飯飽中悟出個道理﹕水土生養民歌﹐民歌貴在本色。相思也罷﹐訴苦也罷﹐阿哥阿妹也罷﹐人家土得心甘情願﹐怡然自得﹐你幹嗎非要逼她改嫁﹖就如《交城山》扔了山藥蛋改姓“華”﹐結果只能換酒錢。 一高興我喝過了量﹐走路像踩上了棉花。小齊便勸我留宿。 (十一) 也許是這酒喝出了點思想﹐一整夜都睡不安穩。恍惚之中﹐似乎被扔上了一座孤島。舉目四望﹐週圍是滿滿一海的水。海水剛纔還呈灰綠﹐轉眼卻變成了紅褐。 想起來了﹐這是紅海。 一陣恐懼。 慌亂中徒勞地掙扎﹐想喊卻喊不出聲來。漲潮了﹐孤島越來越小。不行﹗不能就這麼葬身紅海﹐我得走出去﹗正急得束手無策﹐猛聽得一聲撕心裂膽如野獸般垂死的吼叫﹐奇跡出現。紅海像被刀劈似地斷裂﹐一條大路劍樣地插在兩堵歡騰的水牆之間﹐直通向遠處隱約的陸地。絕處逢生之時卻死活邁不開步﹐忽見一個人站在路口向我招手﹐就拔腿向他奔去。那人卻走得不慌不忙﹐像是與世無爭的野鶴閑雲。剛要催他快跑﹐只見他悠雅地轉回了頭。 ──肖斯塔克維奇﹖﹗ 我失魂落魄。 他身穿黑色禮服﹐眼睛透過深度近視鏡沒有表情地看著我。他一手掠了掠掛在額前的頭髮﹐另一手搭上了我的肩膀。他的手指像敲鼓樣地打著拍子﹐奇怪地歪著嘴。 濁浪喧囂﹐紅水滔天。 看著我氣喘吁吁的驚愕﹐他不緊不慢地開了口﹕ “兄弟﹐日子還長﹐悠著點。” ……。 (十二) 那年﹐我剛好二十九歲。
芝加哥 [2]﹕歌頌毛澤東的家喻戶曉的頌歌。 [3]﹕原始山西民歌。詳見下文。 [4]﹕1906-1975﹐蘇聯最重要的二十世紀作曲家﹐並對世界文化產生重大影響。 [5]﹕中國大陸著名民歌歌唱家﹐山西平搖人。 [6]﹕《東方紅》系由傳統陝北民歌《芝麻油》重新填詞而來。 [7]﹕《森林之歌》中的歌詞。 [8]﹕風行於中國五十年代的合唱《全世界人民心一條》。 [9]﹕華國鋒於一九八零年被迫辭職﹐華國鋒時代結束。 照片說明﹕ (2)﹕中國一九七六年歌頌華國鋒的宣傳畫 (3)﹕剛剛完成《麥克白夫人》的肖斯塔克維奇 (4)﹕一九四八年批判肖斯塔克維奇等作曲家“形式主義”的大會 (5)﹕肖斯塔克維奇一九四九年在《森林之歌》的首演式上 (6)﹕羅斯托科維奇指揮肖斯塔克維奇的作品 |




